财务造假相关问题研究二:从雅百特财务造假案看财务造假犯罪的罪数问题
2025-09-16
一、问题的提出
财务造假案件中,欺诈发行证券罪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是最为典型且常见的两个罪名。前者规制的是发行阶段的虚假披露,后者规制的是上市后持续信息披露阶段的虚假披露。由于两罪行为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在同一财务链条上容易产生关联,因此成为罪数认定的核心难题。
现实中常见的情形是:公司在上市前编造虚假财务数据以完成发行,上市后又继续在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披露或使用同一虚假数据信息。争议的焦点在于:既然所用“虚假数据”为同一,是否应当将其视为“一次性行为”并择一重罪处罚,还是应当认定为在发行与持续披露两个阶段分别侵害不同法益,从而构成数罪并罚?理论界对此存在不同观点。
二、主要学说
法益说主张以侵害法益的数量作为罪数判断的标准。欺诈发行证券罪保护的是证券发行秩序与一级市场投资者利益;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保护的是证券交易秩序与二级市场投资者的知情权。若同一虚假财务数据既用于发行环节又用于持续披露环节,则分别侵害了两类不同法益,应当数罪并罚[1]。
行为说则以实行行为的数量为判断依据。如果造假行为在实质上只实施了一次,而之后的披露环节不过是对既成虚假事实的继续利用或延伸,则应视为一个整体行为,从而可以认定为一罪并择一重处罚[2]。
意思说(犯意说)强调以犯意的个数判断罪数。若行为人在最初造假时即具有在发行阶段和上市后持续利用该虚假数据的统一犯意,则属于同一犯意支配下的连续实施,应认定为一罪;反之,若在不同阶段产生新的独立犯意,则可能构成数罪并罚。
构成要件说主张以各罪的独立构成要件是否成立为判断标准:虚假财务数据进入招股说明书,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的要件;同一数据进入上市后年报或季报,又构成违规披露罪的要件,因此应分别评价[3]。
此外,还有学者从牵连犯的角度解释该类问题:公司在编造虚假财务数据时通常以上市或再融资为目的,随后在定期报告中维持同一数据的虚假效果也正是为了巩固此目的的实现,保证发行成果和市场稳定。于是,发行阶段的欺诈可被视为“目的行为”,持续阶段的虚假披露则成为“手段”或“结果的延续”。二者之间呈现手段与目的、前后衔接的关系,具有牵连犯的特征,应予择一评价[4]。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罪数处理中的另一核心问题: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进行多次法律评价,可能导致对被告人的重复处罚,违背罪责刑相适应与谦抑原则。因此,在认定罪数时需谨慎防止对同一行为的重复定性与重复量刑[5]。
2024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对该类罪数问题作出明确表述:对于公司、企业利用相同虚假财务数据,先后实施欺诈发行证券行为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行为,属于实施了两个违法行为且分别构成犯罪的,应当对二者同时追究刑事责任。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该文件中提到要“同时追究刑事责任”,但如何评价“两个违法行为且分别构成犯罪”,仍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从《解答》发布前的若干判例看,司法机关对此类问题存在不同的处理模式。
三、案例分析
(一)云南绿大地财务造假案(数罪并罚)
云南绿大地公司的案件属于典型的上市前后使用同一虚假数据并被认定为数罪并罚的实例。绿大地在IPO过程中通过虚构利润、编造合同、进行关联交易与循环资金等方式虚增经营业绩,使企业呈现持续盈利的假象。上述虚假数据被写入招股说明书和财务报表,成为满足上市条件的依据。上市后,公司并未终止造假,而是继续将同一套虚假数据计入年度报告和持续信息披露文件,延续并维持此前虚构的经营成果,误导二级市场投资者。
法院最终认定,绿大地及相关责任人员的行为分别侵害了不同法益,触犯《刑法》第一百六十条(欺诈发行证券罪)与第一百六十一条(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构成两个独立犯罪,应当数罪并罚。
该判决反映了司法机关在早期财务造假案件中从严打击的倾向,将同一虚假数据在不同阶段的使用形式区分开来,分别评价,以保护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不同的法益。
(二)雅百特财务造假案(从一重罪)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雅百特财务造假案。上市前,雅百特在重大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过程中,编造虚增的财务数据并写进了重组报告书、招股说明书等发行文件;上市完成后,公司继续把同样的虚构项目、虚增利润计入 2015年年报、2016年半年报和三季报,使得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做交易决策时,仍然受到同一组虚假数据的误导。2017年12月14日,证监会依法对雅百特及相关人员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决定2017年12月16日,雅百特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证监会认为,上述行为涉嫌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证监会专门与公安机关进行了会商,决定将雅百特及相关人员涉嫌证券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随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09刑初1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实际控制人等人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在雅百特案中,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的事实模式:同一组虚假财务数据既出现在公司用于发行的材料中,也出现在其后续的年报与季报里,从而形成“贯穿始终”的虚假陈述链条。盐城市中院最终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实际控制人等人定罪,法院将上市前后的财务造假看作延续性行为,认为欺诈发行阶段的虚假数据已经被“吸收”进后续披露行为中。该判决有其合理之处。第一,犯罪行为的同一性决定了应作为一罪评价。刑法评价的核心在于行为本身。雅百特在前后阶段所采用的虚假财务数据完全相同,本质上是一次性造假的结果,而非两个独立的造假决策。行为对象、手段和数据均重合,属于“同一行为的不同表现”。因此,从刑法评价角度不宜割裂,应整体视为一个行为。第二,想象竞合理论支撑择一处理。根据刑法理论,若同一行为同时触犯数个罪名,应当择一重罪处罚。雅百特的虚假财务数据既支撑了发行阶段的虚假披露,也延续到上市后持续披露,虽然形式上触犯欺诈发行证券罪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但因行为基础相同,符合想象竞合的特征。此时,择一重罪处罚既能反映行为的全部危害性,又避免重复评价。第三,行为延续性排除了数罪并罚的必要。雅百特上市后持续使用同一虚假数据,并非新的独立行为,而是原始造假的自然延伸,缺乏“期待可能性”。即便上市后存在披露义务,但由于披露内容已经被虚假数据所预设,公司事实上不具备“停止造假、真实披露”的现实可能。因此,将其作为延续行为处理,符合刑法对行为整体性的认定。第四,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避免重复处罚。若对雅百特同时适用欺诈发行罪和违规披露罪,实际上会对同一组虚假数据的危害进行重复评价,导致刑罚过度。通过择一重罪处罚,可以集中评价行为的本质危害,既实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又保证了与社会危害性的匹配。
四、结论
在财务造假案件中,对于同一虚假财务数据贯穿于发行与持续披露两个阶段的情形,应当坚持一罪处理、从一重罪处罚的立场。其一,犯罪行为具有同一性:前后阶段采用的虚假财务数据实质相同,系一次性造假的结果,而非两个独立决定;行为对象、手段和数据高度重合,应整体评价。其二,若同一行为同时触犯数罪,应择一重罪处罚。虽然在上市前后都进行了编造和虚假披露行为,但实质上行为基础相同,符合想象竞合的特征。其三,行为人上市后对同一虚假数据的继续使用并非独立的新行为,而是原始造假的自然延伸,缺乏“期待可能性”。其四,对同一虚假数据同时适用两罪,可能导致重复评价与过度量刑,而择一重罪有助于集中评价行为实质危害、避免刑罚膨胀。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
[2]王志祥,姚兵:《罪数形态研究述评》,载《河北法学》,2008年11月。
[3]周光权,《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论争及其长远影响》,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3月。
[4]高铭暄,叶良芳,《再论牵连犯》,载《现代法学》,2005年2月
[5]肖中华,周军,阎颖,《论刑法中的禁止不当评价》,载《法律适用》,2000年3月
本文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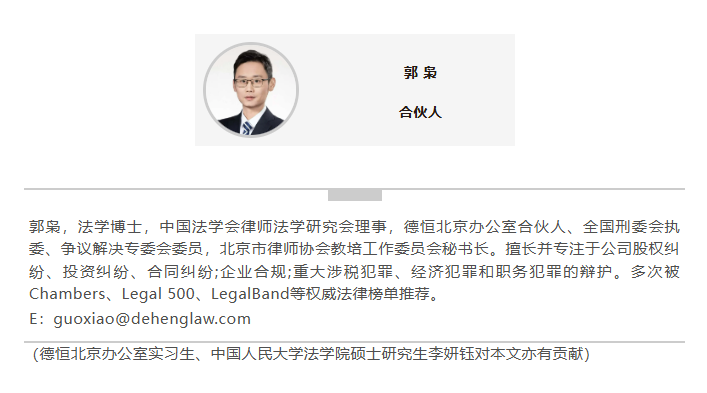
声明:
本文由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创,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德恒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