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蓝天格锐案“维权热”的“冷思考”(三)——关于国际条约在本案中之适用
2025-11-26
内容摘要:
在本文中,我们探讨了在蓝天格锐案中适用国际条约(尤其是《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可行性及其对中国受害者维权工作的潜在价值。我们认为,虽然《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为资产追查、冻结与返还提供了基础性的双边协作框架,但在资产返还问题上,上述条约“不预设前提的协商机制”可能导致请求国处于弱势地位。相较而言,《反腐败公约》第57条第3款第(c)项所设定的“优先考虑返还”机制,虽属酌定性规则,却构成一种“可审查的优先义务”,可在资产处置的谈判中强化请求国的价值主张并确立更有利的目标导向。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上述两项条约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可通过“方向+载体”的方式实现协同适用,以《反腐败公约》确立目标与价值导向,以《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提供程序路径与执行机制。
此外,还应注意到,相关国际条约的作用空间并非仅局限于政府之间的协商谈判等狭窄的领域,不论中国受害者的集体维权最终采取哪种路径,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都将起到很好的价值导向作用,从而在国际条约层面构建起更有利的资产返还论据体系。
前言
在“对蓝天格锐案‘维权热’的‘冷思考’(二)”一文中,我们对蓝天格锐案受害人的相关集体维权路径的选择问题做了探讨,正如我们在该文中所述,基本维权路径的选择是否恰当,往往更具有全局性影响,但“工作目标是否明确且适当”“博弈工具与手段是否得力”等相对细节层面的问题,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最终的维权效果。在本文中,我们兹就相关国际条约在本案中的适用问题进行简要探讨,以期为本案的中国受害者提供一些有力的博弈工具。
一、“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在本案中的适用
(一)“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在本案中的可适用性
中英两国曾于2013 年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下称“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该条约于2016 年生效。
上述条约第1 条第1 款规定,中英两国“双方应当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在刑事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相互提供最广泛的司法协助,包括限制、冻结、扣押和没收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所协助的范围就包括了“进行查询、搜查、冻结和扣押”“涉及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的协助”“不违背被请求方法律的其他形式的协助”等。
上述条约第19 条规定,中英两国“双方应当根据被请求方法律,在涉及确认、追查、限制、冻结、扣押和没收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的程序中相互协助”。
上述条约第20 条第1 款规定,“持有被没收资产的被请求方可以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请求方返还或者与请求方分享该资产或者出售该资产的收益。返还或者分享该资产的条件和安排以及返还和分享的比例由双方商定”。第20 条第2 款规定,“当被请求方没收的资产是公共资金时,且这些资产是从请求方贪污、挪用所得,无论这些资金是否已被洗钱,被请求方应当将没收的资产或出售该资产的收益返还请求方,但应扣除合理的变现费用”。
在本案中,“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以上条款内容,均可以作为相关案涉比特币资产的追查、没收、返还等事宜的法律基础。
虽然从目前的公开信息看,中国公安机关曾“通过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等渠道与英国执法机关深入开展跨境追逃追赃协助”,且“仍在与英国执法机关继续开展跨境追逃追赃合作”,但现有公开文件并未披露更多的细节,因此,目前尚难以确认本案是否以及在何种范围内正式适用了“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然而,我们预计,在本案国际司法合作的推进过程中,尤其是在案涉资产处置的问题上,不论最终将适用哪些国际条约,“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都将是其中关键性的法律基础。
(二)“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局限性
在犯罪所得资产的处置问题上,前述“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第20 条也对此作出了相关规定,由于本案通常并不涉及“公共资金”,故本案主要应适用上述条约第20 条第1 款的规定。
而从前述“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第20 条第1 款的规定看,其对于相关资产的处置同时规定了“资产返还”或者“资产分享”的两种路径,且“返还或者分享该资产的条件和安排以及返还和分享的比例由双方商定”。
可见,在本案中,假设仅适用“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在案涉比特币资产返还的问题上,则通常是由双方采取“不预设基本路径”(即:不预设资产返还或资产分享的路径),“且不预设处置方案”(包括:条件、安排、比例等)的“宽泛性的双边协商机制”。
在上述机制下,虽然双方可以看似平等的地位相互开展协商,但从实际操作角度看,“要求资产返还的”请求国由于并不掌控相关犯罪所得资产,在谈判中难免因此而处于某种弱势地位,而上述“宽泛性的双边协商机制”并无助于改善请求国的上述弱势地位,甚至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加剧请求国的这种弱势地位。
二、“反腐败公约”等其他国际条约在本案中的适用
(一)“反腐败公约”在本案中的可适用性
中英两国同时也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称“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虽然“反腐败公约”的适用对象主要为“腐败犯罪”(例如: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而从现有的信息与资料看,本案的核心犯罪行为主要涉及集资诈骗与洗钱,但本案仍可纳入“反腐败公约”的适用范围。具体而言:
“反腐败公约”第23 条要求缔约国将洗钱列为公约下应刑罚化的犯罪,并支持将洗钱的上游犯罪范围尽量扩大,不必限于腐败犯罪。
“反腐败公约”第31 条第1 款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在本国法律制度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能够没收:(1)来自根据该公约确立的犯罪的犯罪所得;(2)用于或者拟用于根据该公约确立的犯罪的财产、设备或者其他工具。
“反腐败公约”第57 条第1 款规定,缔约国依照该公约没收的财产,应当由该缔约国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和本国法律予以处分,包括“返还其原合法所有人”。
也许并非毫无争议,但从以上各项规定中可以推断出,类似本案这样的“构成洗钱但上游为非腐败犯罪”的案件,也应属于“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犯罪,在本案中“被英国方面扣押”的比特币资产亦属于“反腐败公约”第31 条第1 款第2 项所规定的“应予没收的资产”,上述比特币资产亦应按照“反腐败公约”第57 条的规定予以返还。
与此同时,由于本案案涉的比特币资产并不涉及公共资金,也并非腐败类犯罪的所得,本案主要应适用“反腐败公约”第57 条第3 款第3 项的规定,即:相关资产的处理方式为“优先考虑将没收的财产返还请求缔约国、返还其原合法所有人或者赔偿犯罪被害人”。
(二)在本案中适用“反腐败公约”的益处
“反腐败公约”第57 条第3 款第3 项所设定的“优先考虑返还”,预示着相关资产返还通常属“酌定返还/协商返还”的范畴,英国内政部在其发布的《透明且可问责的资产返还框架》中,也将依据“反腐败公约”第57条第3款第(c)项进行的资产返还视为酌情处理事项。
尽管如此,应注意到的是,“反腐败公约”的上述规定,虽然不具有“强制返还”的刚性约束力,但其并非单纯的道德倡议或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可审查的优先义务”。
具体而言,在“反腐败公约”第57 条第3 款第3 项规定的情形中,受请求国虽然对于如何处置相关犯罪所得资产拥有裁量权,但上述“裁量权”的行使,不得弱化“优先考虑返还”的基本导向与优先次序,不应由于“裁量”而导致应返还的主体/比例被任意背离/压缩,受请求国在决策中应体现出对“返还请求国、合法原所有人或补偿受害人”的实质性的优先评估并说明理由,承担自身决策符合“优先考虑返还”之价值取向的证成负担。
可见,相比于其他国际条约中“宽泛性的双边协商”(甚至是直接规定应进行“分成式的分享”)的操作路径,“反腐败公约”的上述制度框架,无疑为“要求返还资产的”请求国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补充工具。在本案中,如果可适用“反腐败公约”,将更有助于中国方面尽可能的争取案涉资产的返还,并阻击他人觊觎中国受害者的应有利益,使其成为中国方面在本案中的“有力抓手”。
三、“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与“反腐败公约”的协同适用
“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第20 条第1 款侧重于强调“不预设前提的双边平等协商”,而“反腐败公约”第57 条第3 款第3 项更侧重于强调“优先考虑返还”,从表面上看,以上条约的规定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冲突。但实际上,不论从相关条约内容本身或是从国际条约解释规则来看,以上两个条约的规定,都属于并行不悖、甚至相互补充的关系。具体而言:
(一)从相关条约内容看,相关条约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冲突
“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第20 条第1 款规定,被请求方可以“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返还或者与请求方分享资产,并由双方商定具体要求/安排与比例。上述条款内容,所确立的是协商的程序载体与权限边界,并未否定把“资产返还”作为优先目标的做法。
“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第27 条则进一步规定,“本条约不妨碍任何一方根据其他可适用的国际条约或者本国法律向另一方提供协助。双方也可以根据任何其他可适用的安排、协议或者实践提供协助”。
从对上述条款的并行解读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根据《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寻求协助,并不必然排除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7条第3款(c)项的可能性。在我们看来,上述两个条约的内容之间并不存在内在冲突。
(二)从国际条约解释规则的角度看,相关条约也属于并行不悖、甚至相互补充的关系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规定,对于国际条约,应按照条约目的与宗旨并结合“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作善意、系统的整合解释。
在本案中,“反腐败公约”第57 条第3 款第3 项所确立的是在决策时“优先考虑返还”的义务,但其并非自动返还令,需要借助协商/安排等方式将其落地。“反腐败公约”第57 条第5 款甚至还规定,缔约国还可以考虑就所没收财产的最后处分逐案订立协定或者可以共同接受的安排。可见,“反腐败公约”的上述机制,与“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第20 条第1 款所规定的“协商”机制正好互补,二者体现为“方向+配套机制”(“原则+具体执行”)的衔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
鉴于中英两国均为“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在本案中,对于“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第20 条第1 款的规定,即应在“反腐败公约”第57 条第3 款第3 项所规定的“优先考虑返还”的框架下,被解释为一项“实施‘反腐败公约’、细化操作”的程序安排。
换言之,即应以“反腐败公约”第57 条第3 款第3 项所确立的“优先考虑返还/赔偿”作为协商目标与决策导向,而以“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第20 条第1 款作为实现该目标的程序载体。
因此,在本案中,“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与“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不但可并行不悖,且还可起到相互补充与协同的作用。
结语
通过本文的讨论,在国际条约层面已经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明晰、甚至在目标导向方面有利于中国受害者的“资产返还”的框架路径。但是,对于上述框架路径的局限性,也应有清醒的认识。毕竟,目前在本文中所讨论的相关国际条约规定,并未设定“强制返还资产”的条约义务,相关资产的返还尚需借助政府之间的协商与合作予以落实,并因此而可能受到国际政治因素、国际合作机制的有效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并导致最终处理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并且,上述政府之间的协商谈判过程,往往需要历经不少时日,且并非单方国家所能有效掌控,亦导致相关维权所耗费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我们理解,相关国际条约,尤其是“反腐败公约”,其作用空间并非仅局限于政府之间的协商谈判等狭窄的领域。我们相信,在中国受害者维权、尤其是集体维权的工作中,不论最终采取“司法程序主导”或是“行政路径主导”的路径,上述条约的相关规定,都将起到很好的价值导向作用,并形成有效的助力。因此,在本案中,如何通过借力上述国际条约,以更好的维护中国受害者的权益,是值得相关各方高度关注和积极探索的工作。
特别声明:
(1)以上内容,仅供各方研究、学习与探讨适用,不应被视为我们正式出具的法律意见。
由于我们目前掌握的案件资料与信息有限,且其中涉及到大量的关于英国法律规则的适用与判断,虽然我们已经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以尽量避免可能产生的偏差,但文中的观点可能不尽然成熟或准确,其中如有错漏之处,欢迎各位阅读者予以指正;
(2)考虑到相关问题的专业性与复杂性,而本文的阅读者中很可能有相当部分人员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为便于阅读者快速理解与掌握我们希望传达的核心内容,我们对文章部分内容(尤其是部分的法律规则)进行了适当的简化或通俗化的表述,有关各方如需正式使用文中所提到的相关内容,请注意先自行予以核实;
(3)以上内容,大量涉及对英国法律规则的理解与适用,有关各方在判断与处理涉及英国法律的相关问题时,建议应咨询英国相关法律专业人士;
(4)如阅读者对文中内容有相关疑问或对此话题感兴趣,可以按照文章末尾所附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对于大家感兴趣的且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们将适时统一的作出解答。
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一方式,与本文的作者取得联系:
(1)联系邮箱:chencc@dehenglaw.com
(2)微信公众号: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后台留言。
德恒-Gateley “蓝天格瑞项目组”成员简介:

英国Gateley Plc律师事务所服务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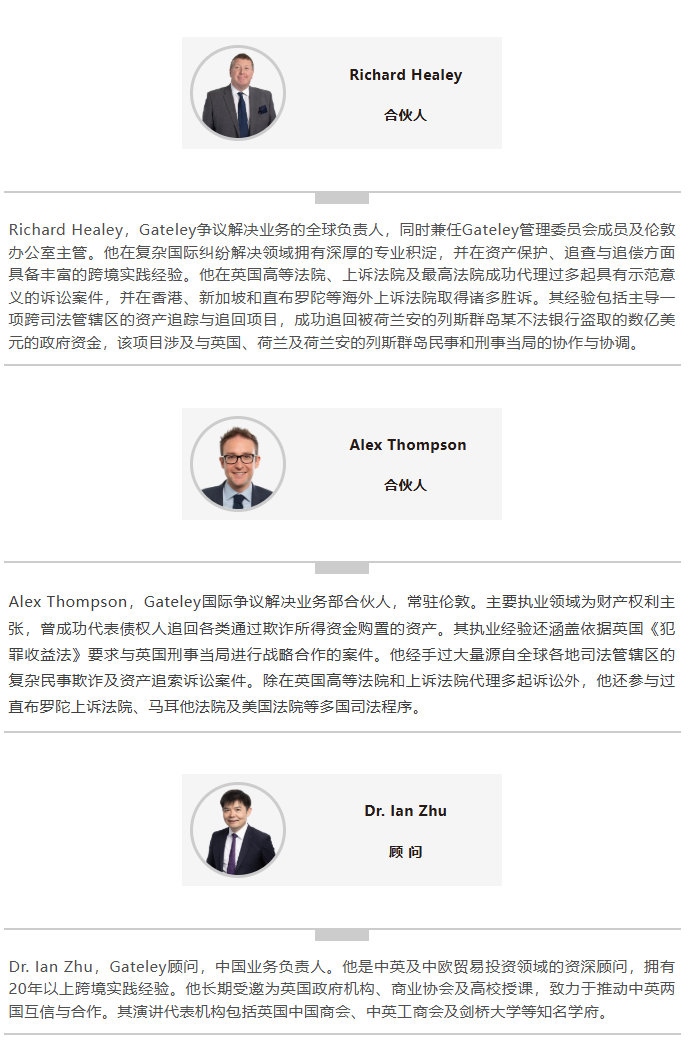
项目组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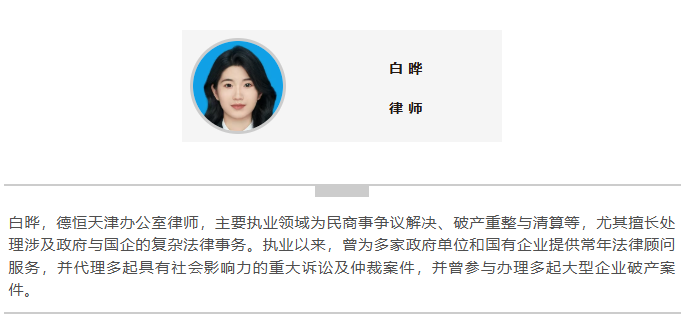
附:英国Gateley Plc律师事务所介绍:
英国Gateley Plc律师事务所位列英国前50强律所,业务网络覆盖英国本土、迪拜及中国香港地区,设有29个分支机构。该所创立于200多年前,并于2015年成为全球首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商事律所。该所在处理高价值、复杂诉讼方面拥有卓越业绩,拥有逾120名专业律师组成的争议解决团队,尤其擅长于代表国际客户在英国及国际法院处理商业与公共事务诉讼。
声明:
本文由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创,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德恒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