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一方或其近亲属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法律救济途径探究
2025-09-19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不使儿童以不当方式与父母一方分离,保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亦是国际社会共识。夫妻双方离婚期间、离婚后或分居期间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不仅严重影响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亦不利于离婚纠纷的和谐化解。《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12条明确规定针对此类行为的受害方既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亦可参照《民法典》第997条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两种制度虽同属具有预防性功能的司法禁令,但在制度定位、适用情形、证明标准上仍存在差异。笔者团队近期收到很多关于分居期间或离婚诉讼期间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咨询,深感有必要探讨这一话题,以明晰两种司法禁令的不同适用情形,故结合以往代理经验及相关研究,梳理成文供参考如下。
一、人身安全保护令和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制度内容及区别
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12条规定,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纠纷解决中,除该条款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和人格权侵害禁令之外,行为保全制度同样也具有一定的预防性作用,行为保全是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为避免当事人合法权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依申请责令另一方作出或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的强制措施。然而,行为保全必须与诉讼程序紧密衔接,当事人若要申请行为保全,往往需要先提起相关诉讼,这在时间上会有所拖延,且通常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其适用性受到一定限制。
与之不同的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和人格权侵害禁令并不以提起离婚诉讼为前提。实践中,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可能发生在离婚诉讼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在离婚后,还可能发生于双方分居期间。人民法院签发禁令的目的是快速制止不法行为,使父母与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让未成年人能够在稳定的亲子环境中生活,而非对离婚、抚养权归属等相关纠纷进行实质性处理,本文亦主要针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和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内容展开探讨。
(一)人格权侵害禁令
人格权侵害禁令是在人格权受到侵害的紧急情况下通过采取事先预防性保护,避免权利主体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针对违法行为人发出的一种命令。根据《民法典》第997条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该制度重在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赔偿,其本质是通过法院预先介入,阻止侵害行为发生或持续,避免权利主体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具有普适性和预防性,不局限于特定身份关系或行为类型。
在婚姻家庭领域,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用可延伸至身份权利的保护。根据《民法典》第1001条规定,对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没有法律规定时,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四编人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是一种重要的身份权。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不仅侵害了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更直接损害了父母一方正常行使抚养、教育和保护权的身份权益,因此,对实施该行为的不法主体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有法律依据。当事人以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应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7条规定依法予以支持[1]。
关于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申请程序,现行法律法规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审理申请人格权禁令案件时,通常会参照《反家庭暴力法》中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详见下文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程序的阐述)。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
1.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确立的专门性司法保护措施,性质上属于民事强制措施,旨在通过法院裁定即时阻断家庭暴力行为,为受害人提供人身安全保护。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内容可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适用范围上,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于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也可以参照适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一般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对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形成重大侵害,可以将该行为视为一种家庭暴力行为,并通过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方式预防和制止。因此,将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规制范畴,具有法律基础。
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申请内容上进一步明确“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可以包括禁止被申请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禁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
2.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程序规则与效力
申请程序上,申请人可以向受害人居住地、致害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中任何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以裁定形式作出,一经作出并送达即具有法律效力,有效期不超过六个月,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
就效力而言,被申请人必须严格遵守保护令内容。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3.人格权侵害禁令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度区别
人格权侵害禁令与人身安全保护令两制度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在婚姻家庭领域的特殊形式,具体表现为:
其一,制度定位与适用范围不同。人格权侵害禁令是《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的一般性制度,适用于所有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及参照人格权保护的身份权受侵害的场景,不受特定身份关系或共同生活状态的限制。而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确立的专门性制度,属于人格权侵害禁令在婚姻家庭领域的特殊形态,其适用范围为“家庭成员之间”及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
其二,侧重场景与侵害程度不同。人格权侵害禁令应对一般性的人格权或身份权侵害,例如抢夺、藏匿子女导致父母一方监护权、探望权无法正常行使的情形;而人身安全保护令主要针对具有紧迫性、危险性的身体或精神侵害行为,如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过程中伴随殴打、威胁、侮辱等身体或精神暴力,其制度更强调对受害人即时人身安全的紧急保护。
基于上述差异,司法实践中需根据侵害行为的性质、主体关系及危险程度,选择适用更契合的制度。接下来,笔者将结合具体实务案例,分析法院在面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时,如何根据具体情境选择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或人格权侵害禁令进行裁判。
二、人格权侵害禁令与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的司法案例分析
(一)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司法案例
案例一: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三——颜某某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中,2015年,颜某某与罗某某(男)登记结婚。2022年7月,颜某某生育双胞胎子女罗大某(男)、罗小某(女)。罗大某、罗小某出生后,与颜某某、罗某某共同生活居住在A省。因家庭矛盾未能得到有效调和,2024年3月,罗某某及其父母、妹妹等人将罗大某强行带离上述住所并带至B省。此后,罗大某与罗某某的父母在B省共同生活居住。经多次沟通,罗某某均拒绝将罗大某送回。颜某某遂提起本案申请,请求法院裁定罗某某将罗大某送回原住所并禁止罗某某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
法院认为,解决分居状态下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问题的前提是及时快速制止不法行为,尽量减少对未成年人的伤害。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可以进行事先预防性保护,避免权利主体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民法典》第1001条规定,对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在相关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人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是一种重要的身份权,人民法院针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签发禁令,能够快速让未成年子女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是人格权保护事先预防大于事后赔偿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对不法行为形成有力的法律震慑。人民法院遂裁定支持了罗某某提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
案例二:申请人以对方抢夺、藏匿子女为由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法院予以支持
由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件中,申请人冉某蜜(女方)与被申请人罗某(男方)系非婚同居关系,二人于2025年2月28日生育一子罗某沅(时年3个月,处于哺乳期)。2025年6月17日,双方因感情纠纷,男方未经女方同意将罗某沅抱走藏匿,女方报警,派出所接处警记录及监控均证实罗某抱走孩子;男方在聊天记录中承认将孩子带离并藏匿,称是为给孩子好环境。女方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男方停止侵害其对罗某沅的抚养权,告知孩子位置并交还,禁止干扰其行使监护权;男方以女方经济条件差、无法提供良好生活环境为由抗辩。
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本案中,罗某未经同意抱走并藏匿哺乳期孩子,侵害了冉某蜜的抚养权,符合申请条件。同时依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父母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法院应支持。罗某的行为属于“藏匿未成年子女”,冉某蜜的申请符合该条款规定。虽然申请人冉某蜜与被申请人罗某平等享有对非婚生子罗某沅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平等享有对非婚生子罗某沅的监护权。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之规定,对于未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应当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本案中,罗某沅仅三个月,需要母乳喂养,双方现因感情问题发生纠纷,也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原则履职监护职责,妥善处理孩子的抚养事宜,故非婚生子罗某沅现阶段由母亲冉某蜜直接抚养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法院最终裁定被申请人罗某立即停止侵害申请人冉某蜜享有的对非婚生子罗某沅的抚养权,即被申请人罗某应当如实告知申请人冉某蜜非婚生子罗某沅的具体住址并配合其送回罗某沅。
案例三:申请人以对方藏匿子女、阻碍探视为由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法院认为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以上事实,不予支持
由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件中,申请人王某某1请求法院裁定被申请人柳某某停止侵害其对婚生子王某某2的监护权,禁止被申请人藏匿子女并阻碍探视权的民事案件。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自2022年12月起擅自藏匿子女,阻碍其探视,严重侵害其监护权及子女身心健康;被申请人则辩称未阻止探视,且已告知子女居住及幼儿园地址,愿意配合探视。法院依法审理后驳回申请。
法院认为,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申请人应就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事实具有较大可能性承担举证责任。申请人诉称2022年12月16日起被申请人带走并藏匿孩子,并提交报警记录等证据主张被申请人阻碍其行使探望权。但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申请人于2023年11月份对婚生子王某某2进行过探望,且经询后申请人能够明确自述目前婚生子王某某2具体所在的幼儿园地址和居住地址,故申请人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被申请人藏匿孩子的事实。在案件受理过程中,申请人表示双方现已对婚生子的探视进行了相互的沟通,且被申请人亦主动配合申请人对婚生子王某某2进行了多次探视,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申请人的探望权受到阻碍。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申请人藏匿子女及阻碍探望权,故不符合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条件。
(二)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司法案例
案例一:申请人以其公婆抢夺、藏匿未满二周岁子女为由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予以支持
由河北省东光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件中,申请人袁某英与被申请人孙某、邱某凯系儿媳与公婆关系,袁某英之夫邱某朋(孙某、邱某凯之子)于2024年10月17日去世,二人育有女儿邱某沫(未满两周岁)。2024年11月18日,孙某、邱某凯在未征得袁某英同意的情况下,将邱某沫强行抱走并藏匿,拒绝告知孩子去向,袁某英多次寻找并报警未果。袁某英认为二被申请人的行为侵害其对邱某沫的监护权、抚养权,不利于孩子成长,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停止侵害、归还孩子并由其抚养。
法院认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袁某英作为邱某沫的母亲,其监护权受法律保护。二被申请人未经同意抢夺、藏匿邱某沫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了袁某英的监护权,且割裂母女亲情,可能对未成年人心理造成伤害。尽管二被申请人失去儿子的悲痛可予理解,但不得以此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据此,法院支持袁某英的申请,裁定二被申请人停止侵害监护权、抚养权,并将邱某沫带回申请人处抚养。
案例二:申请人以对方抢夺、藏匿子女为由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予以支持
由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件中,申请人陈某某与被申请人王某某原系夫妻,2019年11月生育女儿陈某甲,同年12月协议离婚,约定陈某甲由陈某某抚养,王某某不支付任何费用。2024年12月,王某某起诉变更抚养权被法院驳回。2025年6月13日,王某某未经陈某某同意,擅自将陈某甲从就读幼儿园接走并藏匿,未送回学校上学,经报警后仍拒不归还。陈某某以王某某抢夺、藏匿子女侵害其抚养权及女儿受教育权为由,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王某某送回女儿并禁止侵害其受教育权和人身安全。
法院认为,申请人陈某某作为陈某甲的直接抚养人,其承担对陈某甲抚养、教育、保护义务的同时,亦享有对陈某甲进行监护的法定权利,被申请人王某某作为陈某甲的母亲,如需要探视陈某甲或者将其接走共同生活,应当与陈某某友好协商解决,而不能未经陈某某许可就擅自带走陈某甲,使陈某甲脱离陈某某的监护,既是对陈某某权利的侵犯,亦是对父女亲情的严重割裂,也会对陈某甲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因此,申请人陈某某要求被申请人王某某将陈某甲送还给申请人陈某某,并禁止被申请人王某某实施侵害陈某甲的受教育权和人身安全行为的申请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三、人格权侵害禁令或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选择
结合以上案例分析可知,当面临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时,当事人既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亦可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进行救济。但实质上两者功能仍有不同,适用的场景虽有交叉但仍需明确相应定位以更好化解纠纷
(一)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用更侧重一般性身份权侵害,通常满足以下条件
1. 主体关系不限定“家庭成员或共同生活者”:无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否为家庭成员(如非婚同居关系、已离婚且不共同生活的父母),只要存在抢夺、藏匿子女导致监护权、抚养权受损的情形,均可适用。例如案例二中,冉某蜜与罗某为非婚同居关系,法院仍支持其基于抚养权受侵害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例一中,颜某某与罗某某虽为夫妻,但被申请人还包括罗某某的父母、妹妹等近亲属,法院基于身份权保护的一般性规定签发禁令。
2. 侵害行为未达到“家庭暴力”程度,但具有紧迫性:若抢夺、藏匿行为未伴随暴力、威胁等直接人身危险,仅干扰监护权行使,如擅自抱走孩子拒绝送回、哺乳期孩子被迫脱离母亲等行为,但该行为亦会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亲子关系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则可以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例一、二中,被申请人虽未实施物理暴力,但行为已导致未成年人脱离法定监护,法院均支持了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
3. 需充分证明“侵害正在发生”:申请人需提供证据证明抢夺、藏匿事实,如报警记录、监控录像、被申请人承认藏匿的聊天记录等,否则可能因证据不足被驳回,如案例三,王某某1因无法证明被申请人藏匿子女,且被申请人亦主动配合申请人对婚生子王某某2进行了多次探视,其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未获法院支持。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则更需要考虑暴力及遭受暴力的现实危险因素,需满足以下条件:
1. 主体限定于“家庭成员或共同生活者”:被申请人通常为配偶、父母、子女等家庭成员,或虽非家庭成员但曾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如公婆、岳父母)。例如案例一中,袁某英与被申请人(公婆)因配偶(被申请人之子)去世前曾共同生活,属于“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案例二中,陈某某与王某某为已离婚的父母,虽不共同生活,但基于父母与子女的家庭成员关系,仍可适用。
2. 侵害行为关联“家庭暴力”或具有“即时人身危险”:若抢夺、藏匿过程中伴随暴力(如强行抱走时推搡殴打申请人或孩子)、威胁(如拒绝告知孩子下落并言语恐吓),或行为本身对未成年人构成现实危险的,法院可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例一中,公婆强行抱走孩子并拒绝告知去向,导致袁某英无法行使监护权,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对监护权的侵害,且可能对未成年人心理造成伤害,支持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案例二中,王某某擅自接走孩子并阻止其上学,法院以“侵害受教育权及人身安全”为由支持保护令。
(三)总结:以侵害性质及主体关系为核心判断标准
司法实践中,对人格权侵害禁令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选择上,首先,审查主体关系与行为危险性,若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属于“家庭成员”或“共同生活者”,且抢夺、藏匿行为伴随暴力、威胁等直接人身危险,或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构成紧急侵害,则优先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选择既契合该制度对存在暴力因素场景的专门规制,也能通过其更强的执行力快速阻断危险。其次,若主体关系超出“家庭成员或共同生活者”范畴,或行为未直接涉及人身危险,但已实质性干扰监护权、抚养权的正常行使,且该损害难以通过事后赔偿弥补的,则应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同时,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过程中,若一方为争夺抚养权,散布对方个人信息,或是在家中安装监控监视另一方、侵扰并泄露另一方隐私,也可通过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方式,全面保护监护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利。
四、总结与建议
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14条规定,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本条第1项或者第2项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法院在确定抚养权时始终以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为核心,抢夺、藏匿这类忽视子女的真实意愿与成长需求的方式,不仅不利于取得子女的抚养权,反而会成为法院考量其是否具备适宜抚养条件的负面因素。最终导致行为人得不偿失,既未能实现争夺抚养权的目的,又给孩子的成长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对于遭受对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切勿采取同样激进的方式进行对抗,也不要被动等待,应保持理性,积极采取合法措施维护自身与孩子的合法权益,全面、及时地固定相关证据,例如双方就子女抚养问题沟通的微信聊天等电子记录,目睹抢夺行为发生的邻居、亲友或学校工作人员等出具的证人证言,事发地点的监控录像,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获取的出警记录、询问笔录等。包括对方在抢夺过程中使用暴力造成伤害等情况,留存己方或子女的伤情照片、医疗机构的诊断书、病历,这些证据不仅是清晰呈现对方侵害行为的关键,更是后续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人格权侵害禁令时不可或缺的支撑,能够帮助法院快速查明事实,及时作出对己方有利的裁定。
尽管“二令”的适用场景各有侧重,但核心目标始终统一于“及时制止不法行为、维护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及申请人合法权益”,为解决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纠纷提供精准有效的救济路径,当事人则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安全、监护权受损等因素灵活选择。
最后,笔者在此建言,夫妻双方的离婚纠纷不应使未成年子女成为争夺或对抗的工具。在处理抚养权争议时,双方应始终秉持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摒弃个人情绪与对抗心理,优先考虑孩子的成长需求与真实意愿,通过协商、调解等平和方式解决分歧,即使无法达成一致,也应在法律框架内理性主张权利,避免采取抢夺、藏匿子女等可能激化矛盾、伤害孩子的激进手段。为孩子营造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减少家庭破碎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帮助双方在纠纷解决后更快回归正常生活,避免因长期诉讼消耗精力与情感。希望每一位父母都能以孩子的未来为重,尊重法律规定,尊重亲子关系的本质,通过合法、理性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与孩子的幸福,共同守护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5年版。
本文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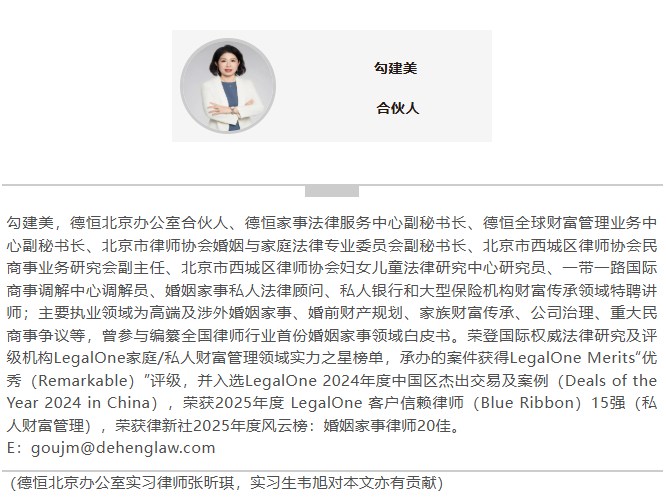
声明:
本文由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创,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德恒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