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民事上诉案件2024年第118, 119, 120及121号剖析公证债权文书在香港的强制执行效力
2025-08-21
案件索引: [2025] HKCA 462
前言
2025年5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就民事上诉案件2024年第118, 119, 120及121号作出判决书,认为内地法院根据公证处《执行证书》所作出的《执行裁定书》不属于香港法例第597章《內地判決(交互強制执行)条例》(“该条例”)可登记的内地判决,债权人因此无法通过法定登记制度在香港法院登记该《执行裁定书》。
案件背景
原告A公司(“原告”)与借款人B(“借款人”)于2019年签订了4份贷款协议(以下统称为“贷款协议”)。同日,保证人C(本案被告)与原告为担保上述贷款协议的履行另行签订了4份保证协议(以下统称为“保证协议”)。保证协议约定,双方均自愿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北京公证处”)申请对该协议办理强制执行公证,并自愿接受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而无需经过诉讼程序。因借款人和保证人无法如期偿还贷款,原告遂向北京公证处申请并取得《执行证书》,并依据该《执行证书》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北京法院受理后于2020年1月发出执行通知书,要求借款人及保证人(本案被告)履行《执行证书》所列之法律义务。后因原告与借款人、保证人(本案被告)达成和解,北京法院裁定终结本轮执行程序。后经原告申请,北京法院于2020年3月恢复执行,并开展新一轮执行程序。2020年12月1日,北京法院就每宗执行案件分别出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在香港的执行程序
2022年11月,根据该条例,原告在香港以单方面申请的方式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登记及认可北京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并于2023年3月获批登记令。2023年3月31日,被告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简称“原讼法庭”)申请撤销该登记,主要包括以下三项理由:
(1)《执行裁定书》并非由该条例第5(2)(a)条中的“指定法院”所作出;
(2)《执行裁定书》并未饬令缴付一笔款项 (No Payment Order),不符合该条例第 5(2)(e)条对内地判决书的要求;
(3) 在内地法律程序中的被告并未现身于北京法院抗辩,且因内地没有进行诉讼程序而未被传唤到庭。因此应根据该条例第18(1)(f)(i)条撤销该登记。
原讼法庭支持上述第二个理由,即《执行裁定书》并未饬令缴付一笔款项,并命令撤销《执行裁定书》的登记。本案原告不服原讼法庭撤销登记的决定,遂向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简称“上诉法庭”)提起上诉。
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的判决
首先,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深入分析及考虑了《执行裁定书》在内地法律程序的性质。根据专家证人的意见,原告在内地的执行程序属于直接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实际上由公证处审核及确定,然后由内地法院强制执行。除非当事人基于特定理由提出异议或反对执行的申请或诉讼,否则内地法院不会介入所涉权利义务的裁决。原告所采用的内地执行程序并不涉及诉讼。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认为这是香港不存在的制度。
其次,根据该条例第5(2)(e)条要求,判决书须饬令缴付一笔款项。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就《执行裁定书》是否饬令缴付一笔款项的问题展开了详细分析,并判定本案所涉的《执行裁定书》并不符合相关要求,理由包括:
· 原告并非内地判决确定的债权人,其要求执行的并非任何判决而是公证债权和义务。
· 执行标的是由北京公证处所发出的《执行证书》中载明,具体金额是由北京公证处决定,并非由内地法院裁判决定。《执行裁定书》实际上仅执行内地公证处的文书。
· 《执行裁定书》的实际意义和功能是结束某一轮执行程序,这显然是内地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法律和行政上的必要之举。《执行裁定书》中所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享有要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及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的权利,被执行人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的义务。”最后一句仅是对现状的一个描述,而非确定支付义务的一个判决或命令。
· 再者,《执行裁定书》表明本案原告有权向内地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相关执行仍是指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上诉法庭认为没有任何内地法律依据表明该裁定书本身可以成为未来强制执行程序的执行对象。
· 另外,如果每次内地法院在执行程序结束后在其作出的裁定书中表明被告仍有未尽之义务,原告可基于此裁定书而得以重新计算2年的登记期限,将不符合该条例的立法原意。
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最终驳回本案原告的上诉,确认原审法官认为《执行裁定书》不符合该条例第5(2)(e)条的要求的决定。
实务意义
随着香港法例第645章 《内地民商事判决(相互强制执行)条例》于2024年1月29日正式生效,以及香港与内地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更便利安排,民商事判决在香港和内地的跨境执行日益频繁,为取得法院判决的判定债权人带来更大保障。
在本案中,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深入分析及考虑了公证债权文书的性质,突显了香港和内地跨境执行民商事判决的法律程序中涉及两地法系的相互理解的特征,也为两地跨境强制执行民商事判决带来了以下一些实务启示。
1.及早进行全面的香港资产及债务调查
区别于内地法院,申请执行人需要主动向香港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程序并提供被执行人的资产和财产线索。香港法院本身不会主动查找被执行人的资产和财产线索,只会基于申请执行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处理强制执行的申请。如交易一方为香港主体,当事人在进行跨境交易或者发生跨境争议的案件初期时,应尽早对该香港交易主体进行全面的香港资产及债务调查,取得其在香港可供执行的资产线索,以便未来在香港申请执行。
2.了解两地法律要素,就跨境争议解决和执行制定合适及相辅相成的诉讼策略
本案中,香港法庭驳回原告上诉的原因之一为内地公证债权文书不是内地法院经司法审判程序作出的判决,不符合法定登记制度的认可条件。可见,在处理内地判决或公证债权文书在香港执行的申请中,香港法庭很多时候都会考虑相关内地文书及内地法律程序的细节,甚至听取内地法律专家就相关内地法律的意见。在实务操作上,内地判决或公证债权文书能否在香港法院取得执行,体现在两地法律从业者充分协调沟通的重要性。若案件涉及内地和香港,为应对跨境案件复杂性,当事人在案件初期应尽早了解两地法律要素,以制定周全的诉讼策略。因此,如发生跨境争议,如债务人在香港有资产,有境外追索可能性的,在内地提起法律追索程序时,亦应咨询香港律师了解香港法院执行内地判决的要求,从而就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追讨债务及执行程序制定相辅相成的策略。
3.如不符合法定登记制度的认可条件,判定债权人可以透过普通法向香港法院寻求救济
香港实行普通法法系,如内地民商事判决或公证债权文书不符合法定登记制度的认可条件,判定债权人还可以透过普通法寻求救济。在普通法的途径下,判定债权人可以在满足相关法律要求的情况下,以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标的或内地判决所判定的债项作为诉因,在香港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寻求香港法院针对被告作出判决。如果被告所诉的抗辩没有任何合理理由或论点支持,原告可以向法庭申请作出被告人败诉的简易判决,以省却全面审讯的开支。
综上,无论债权人是通过诉讼从法院取得判决或经公证程序从公证处取得公证债权文书,均应尽早咨询熟悉香港和内地两地法律的律师,以制定合适及便捷省时的跨境执行策略。德恒律师事务所(香港)有限责任合伙(德恒香港)具有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交融的鲜明特色,擅长为跨境、跨法系的商业活动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2025年3月7日,德恒香港成立跨境执行业务中心,旨在为境内外客户解决“执行难”问题,将立足香港,积极整合境内外跨境调查资源、执行资源,凭借其专业化的跨境执行法律服务团队,为境内外客户提供一站式跨境执行服务。
声明:
本文及其所包含的信息仅供教育和一般参考之用,旨在为公众提供对相关案例或议题的大致理解 ,不得视为作者或德恒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或建议。读者不应在未寻求专业法律建议的情况下根据此信息采取行动。本文不一定反映任何法院或法律机构的官方政策或立场。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
特别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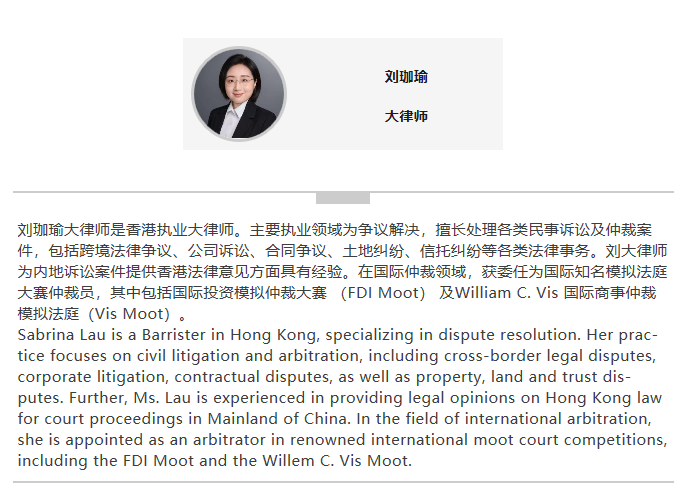
本文作者:


声明:
本文由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创,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德恒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