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
2023-07-25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股权交易日益频繁,随之而产生的纠纷不断涌现。股权转让纠纷中的法律问题呈现出民法与商法两大领域的特征,其中当事人的争议通常集中在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是否受到侵犯、国有股权转让的程序问题、股权转让协议性质的变化、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可以解除或可撤销等问题,笔者结合办案经验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相关案例对相关规则予以分析总结,以期为法律实务提供指引。标的股权在夫妻共同财产制语境和股权代持语境下产生的争议是实务当中的难点,本文主要从以上两个角度对司法实践案例及其中的法律问题展开分析,总结司法实践中共性的争议焦点和应对策略。
一、标的股权在夫妻共同财产制语境下的争议焦点及应对策略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不仅是一个公司法范畴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婚姻法范畴的问题。股权具有特殊性,是集身份、财产与管理等权利于一体的独立的权利形态。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股权(约定分别财产制情形除外),其获得依赖于夫妻共同财产,产生的收益为家庭生活提供支持,也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管辖”范畴中。故,未经配偶同意,转让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股权,极易产生配偶对标的股权提出权利主张从而影响股权转让效力的情况。配偶提起确认之诉,要求确认另一方擅自转让股权的协议无效的诉讼近年来屡见不鲜。司法实践中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制下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认定,通常会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考量:
(一)夫妻共同股权性质的认定
股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身份和地位而享有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同时具有财产性与非财产性。我国法律对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共同财产投资取得的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股权性质没有明确规定。在夫妻共同财产这一概念下,夫妻双方对财产的共有既包括自益权,也包括共益权,因此将夫妻一方名下股权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是有理论依据及现实意义的。根据我国《民法典》以及司法解释,结合司法实践判例,可以总结得出:一般说来只要该股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且无相关分割协议,法院原则上会将股权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案例一:(2019)京01民终8421号案件——彭涌等与黄浩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中,北京市一中院认定:陈玉霞取得的江一湖公司的股权,系于其与黄浩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且黄浩与陈玉霞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并无相关分割协议,故陈玉霞名下的江一湖公司的股权系其与黄浩夫妻共同财产。
案例二:(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2854号案件——邢晓洁等与尤春仓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中,北京市二中院认为涉案股权系邢晓洁与尤春仓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为夫妻共同财产。
案例三:(2006)浙民二终字第181号案件中,浙江省高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和查明的事实,认定:被告出资988万元于安深公司是在其与原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被告在案涉公司拥有的股份在转让之前当然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
但也有少数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极强的人合性,股权同样也具有较强的身份专属性,故而股权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畴。如(2018)京03民终12607号中,北京市三分院在二审判决书中指出:即使是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而取得股权,但是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股权本身也并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只能是股权代表的价值利益和所带来的收益,未登记一方不属于股权的共有人。
(二)夫妻单方转让股权行为效力的认定
由于夫妻双方对于股权的共同共有关系仍未获得立法上的承认,未经配偶同意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构成无权处分行为也成了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对于此种情况,司法实践裁判观点不一。
有的法院认为,夫妻一方未同意转让夫妻共有股权的,转让行为是无权处分行为,对不同意方不发生效力。比如上述(2006)浙民二终字第181号中,浙江省高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和查明的事实认定:被告出资988万元于安深公司是在其与原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被告在案涉公司拥有的股份在转让之前当然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共有属于共同共有,如果没有特别约定,对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须征得全体共同共有人的同意。被告要处分本案诉争的财产,须征得原告的同意。在原告未同意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确认被告与二被告于2006年3月1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
在(2019)京01民终8421号中,北京市一中院认为被告向二被告转让被告名下的江一湖公司的股权,系无偿转让,属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被告就涉案股权的转让应当与原告平等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现原告对于股权转让并不知情,被告与二被告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将江一湖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系无权处分行为。
但也有法院考虑到股权的特殊属性,认为股权登记所有方转让股权的行为并不需经过另一方同意,不属于无权处分,转让后获得的对价即为夫妻共同财产。在(2020)湘01民终11504号中,关于被告转让涉案股权是否构成无权处分的问题,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除其具有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行使,不受他人干预。在股权流转方面,我国《公司法》亦确认股权转让的主体为股东个人,而非其家庭。故被告作为长沙浩鼎投资有限公司、长沙含浦高纯石墨制品有限公司的股东,有权决定是否转让其所持股权,原告作为被告的配偶,无论其对于股权转让同意与否,对于股权转让的效力均不构成影响,但被告因股权转让而获得的对价,仍属于原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
综上可知,对于“夫妻双方共有的是股权还是转让股权所获的对价”“未经配偶同意转让名下股权的行为是否属于无权处分”“无权处分未经追认是否直接导致协议无效”这三个问题,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亟待司法解释的完善。
(三)股权转让受让人主观“恶意”的认定
实践中,有法院直接将股权转让双方当事人的行为认定为恶意串通从而直接否认协议效力,通过分析股权的定价、交易双方的身份关系、交易习惯和股权转让程序等事实来认定受让人与实际出让人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
在(2020)湘01民终11504号中,长沙市中院虽认为无论原告对于股权转让同意与否,对于股权转让的效力均不构成影响,但长沙市中院仍认为二被告是否在签订涉案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时有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将直接决定涉案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根据其查明事实,原告在离婚时仍与被告一协商股权分割事宜,并未放弃相关权利,亦不知道被告一将本案所涉股权转给被告二,且两被告系母子关系,两人签订关于上述两个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没有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对价,且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原被告签署《离婚协议》两个月前所签订,两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依据上述事实及证据,可认定被告一具有通过股权转让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故意。此外,被告二并非善意第三人,从当事人身份关系看,被告二系被告一的母亲,其对原被告的婚姻状况应有一定的了解,其受让股权时所承担的注意义务应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人,但是被告二受让股权时未对股权转让价格进行评估,亦未支付股权对价款,主观上不具有善意。故,一审法院据此认为两被告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
在(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2854号中,北京市二中院认为:涉案股权系邢晓洁与尤春仓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为夫妻共同财产。邢晓洁在其与尤春仓就涉案股权为共同共有关系的情况下,未征得尤春仓同意,将股权转让给邢文波。邢文波作为邢晓洁之弟,其对涉案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及邢晓洁转让行为未征得尤春仓同意应当知情。因此,邢晓洁与邢文波于2011年7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损害了尤春仓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权,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之情形,应当确认无效。
由此可见,若股权受让人与出让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股权转让对价款低于市场价,股权转让对价未支付,转让时间在离婚之前或者离婚程序进行中,法院一般会考虑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为避免争议,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当事人应当合理定价,保证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完备,及时催收股权转让的对价并妥善保留相关凭证。
二、标的股权在代持协议语境下的争议焦点及应对策略
所谓股份代持(也称委托持股、隐名持股、股权挂靠)是指实际出资人(即被代持人)与名义出资人(即代持人)以协议或其他形式约定,由名义股东以其自己名义代实际出资人享有和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由实际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并享有投资权益的一种权利义务安排。
(一)代持协议语境下股权转让纠纷常见的争议问题
在实践中,由于代持人具有完备的权利外观且法律规定代持协议不产生对抗效力,代持人擅自转移股权而实际出资人“哑巴吃黄连”的情况屡见不鲜。代持人若欲主张转让协议无效,首先需要证明自己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其次,还需证明受让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恶意串通。
1.代持关系的认定
“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这一法律事实的证明责任由实际出资人负担,在认证这一法律事实时,法院通常会审查“代持协议”和“实际出资人”这两个要素。以本团队代理的(2019)湘0104民初17242号案件为例:
我方原告常青春公司主张:第三人陈弟(化名)伪造常青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哥(化名)的签字及公司印章,与被告胡某某(陈弟之妻)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常青春公司所占美康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胡某某,陈弟及其妻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常青春公司权益,请求确认常青春公司与胡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胡某某则辩称常青春公司仅为案涉美康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股东为第三人陈弟,陈弟在美康公司初设之时请求常青春公司代陈弟出资100万元获得美康公司股权,事后陈弟向常青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哥返还了注册资金100万元,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分析:
原告常青春公司提交的在美康公司成立之初的支付注册资金的付款凭证以及注册资料以及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等可以认定原告常青春公司才是美康公司的原始股东,第三人陈弟只是美康公司聘请的经理。
被告主张美康公司成立之后陈弟已向常青春公司返还了注册资金100万元,但被告提交的常青春公司法人陈哥的收据上的备注和字样仅能证明陈哥与陈弟的账户之间有金钱往来,但并不能证明各笔款项的性质及相应的数额。结合常青春公司与美康公司之间具有业务往来,陈哥作为常青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及陈弟作为美康公司经理的身份,被告提交的收据也有可能是两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款,而非陈弟返还常青春公司出资。由此,被告提交的收据无法证明陈弟返还常青春公司出资的事实,法院对被告主张的“陈弟与常青春公司之间存在代持关系,陈弟才是美康公司的实际出资股东”的法律事实不予认可。
陈弟和常青春公司之间并没有任何形式的股权代持协议或者代出资协议,而胡某某提供的收据所涉款项性质不明,亦不能证明陈弟与常青春公司之间发生过“常青春公司代陈弟垫资后陈弟返还出资”的事实,因此,既不存在代持协议或代出资协议,亦不能证明股权是由陈弟实际出资,故而法院对被告所主张的代持关系不予认可。
当然,除了这两个直接要素,公司其他股东的实际认可作为佐证代持关系的间接因素,也会对法官的自由心证产生影响。如果隐名股东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其身份已经得到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认可,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佐证其隐名股东的身份。根据实践,笔者总结出能够体现公司及其他股东认可的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1)公司是否向隐名股东发送参加股东会会议的通知;(2)股东大会记录、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中是否有能确定参与股东会、行使表决权人员的身份信息;(3)公司是否向隐名股东发送受领公司分红的通知;(4)公司是否向隐名股东发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5)显名股东是否按照隐名股东指示返还公司分红等收益(注意与借款等其他资金往来相区分);(6)显名股东对股东会决议事项的表决及签署是否有隐名股东授权;(7)显名股东是否曾向隐名股东汇报公司经营情况或询问决策意见;(8)隐名股东是否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或者不担任任何职务却直接参与公司经营决策;(9)公司及其余股东对于股权代持事项知情且认可的邮件、往来函件、短信及微信沟通记录等材料。但是,公司及股东的认可并不能单独证明代持关系的存在事实,至少需要有“代持协议”和“实际出资”两者之一作为直接证据,“公司及股东的认可”才能够发挥其佐证作用。
若法院认定股权出让人不存在代持情况,则无所谓“恶意串通侵害实际出资人利益”的讨论;但是,名义股东与他人订立合同的行为亦不受代持身份的影响,为有权处分,这意味着即便法院认定了代持关系的存在,实际出资人也还需证明受让方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实际出资人利益”的情况,才能实现宣告合同无效的目的。
2.出让方与受让方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
法定的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需要两个构成要件:双方侵害第三人权益的一致意图和损害后果。司法实践中,争议通常在于双方一致的恶意和协同行为的认定。
仍以本团队代理的常青春公司与胡某某这起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纠纷为例,由于法院对常青春公司与陈弟之间的代持关系不予认可,故陈弟对常青春公司所持美康公司的股权并不享有处分权,陈弟签订《股东股份转让协议》的行为系无权处分。本案中,法院从股权转让协议签章的真实性、股权转让对价的支付情况、无权处分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身份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定陈弟与胡某某之间存在恶意串通:
(1)签章的真实性
(2)股权转让对价的支付情况
《转让协议》及美康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档案均显示双方约定了股权转让协议对价为153万元,而经法院调查及双方当事人认可,胡某某从未向常青春公司支付对价即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3)无权处分人和受让人对对方权力情况的知情程度
无权处分人陈弟与受让人胡某某为夫妻关系,胡某某对于陈弟不是协议当事人这一事实具有绝对了解,对对方转移常青春公司股权的意图也具有充分了解。法院通过第一点分析得出陈弟存在转移常青春公司股权的主观恶意,通过第二点认定受让人明知股权转让不真实仍与其完成股权变更,通过第三点认定受让人明知代签人的真实身份以及签章的不真实仍与其签订协议,存在明知故犯的主观恶意。由此法院认定两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转移常青春公司的股权,损害了常青春公司的利益,并据此认定《转让协议》无效。
类似案件还有很多,比如在(2019)京0115民初3782号——上海国电投资有限公司与陈宗耀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华美公司向陈某转让的股权比例增加了,但转让对价却大幅度减少。而且,据以确定国电公司与华美公司股权转让价款金额的《评估报告书》系在2018年8月31日作出,而华美公司与陈某是在2018年12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4个月的时间里股权转让价格发生大幅度变动,华美公司应当对此作出合理说明。诉讼中,华美公司未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说明或提供相关证据。此外,经陈某认可,陈某对于华美公司与国电公司在协议履行中的争议是知情的。综上,该院认为案件事实可以证明华美公司与陈某主观上存在恶意串通。此案中法院同样也是通过价款的支付情况,受让人与出让人的主观认识情况等因素来判定“恶意串通”的存在与否。
因此,法院在认定恶意串通时会从签章真实性、对价的支付情况以及交易双方对彼此权力情况的认识程度加以认定。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证据规则》《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恶意串通”是民事诉讼中为数不多的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最高证明标准的法律事实。通过“恶意串通”的路径主张名义股东与第三人的转让协议无效,并非易事。
(二)应对策略及建议
为避免名义股东以其自己的名义擅自出让股权背叛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人应当尽可能保留完整的出资凭证,无论是实际出资原始取得股权还是请求名义股东代出资之后偿付出资继受取得股权,实际出资人都应当在转账凭证上备注完整的汇款目的并要求对方在出具收据时注明收款事由。同时,为代持事由转账时应避免与其他业务事由合并汇款,以免在出现纠纷时难以认定实际出资数额,影响法院判定。
除此之外,代持协议在认定代持关系上也是决定性的,实际出资人应与代持人签订书面的代持协议,并详细约定代持期间、代持标的等关键内容。在实际出资人直接转让股权的场合,可考虑将名义股东作为一方当事人列入协议中,以免事后名义股东宣称实际出资人伪造签字盖章和委托材料并与受让方恶意串通,挑战转让协议效力,损害实际出资人的合法权益。
三、结语
股权转让制度一方面畅通了股东收回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为潜在投资者基于其利益需求提供了途径,它使得社会财富得以流转,市场经济更加活跃。但是,仅靠市场经济自身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不容忽视。近年来,股权转让纠纷已经逐步成为公司法案件的主要类型之一,矛盾日益尖锐,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关注度日益提高。本文以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为题,以实践中的案例为视角揭示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争议焦点,对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夫妻共同财产的股权和存在代持的股权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和总结,希望能为律师实务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引。
本文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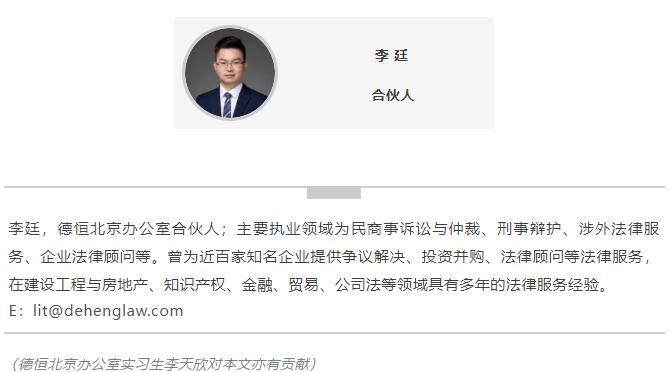
声明:
本文由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创,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德恒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