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关于财务造假上市公司高管“违法薪酬退回”新规解读
2025-10-24
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八十五条【违法薪酬退回】规定: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或者隐瞒重要事实,公司请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退回与其业绩不相匹配的超出合理标准而获得的薪酬或者股权、期权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该条属于新增条款,规定了“违法薪酬退回”,打破了以往上市公司被发现存在财务造假问题时,董事、高管“薪酬照拿、责任不担”的困局。
该条规定也触发了很多业界讨论,围绕以下几个核心问题,笔者进行调研分析,形成以下浅见。
该条款旨在解决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中“劣迹高管”却仍保留高额绩效薪酬的不合理现象。它为公司提供了一条直接的法律武器,追索基于虚假业绩而支付的不当薪酬,是对《公司法》关于董事、高管忠实勤勉义务以及《证券法》相关规定的司法细化,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其在权利主体、认定标准等方面仍有待明确和完善。
一、“违法薪酬退回”条款对于维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权益,惩戒未勤勉尽责董事、高管,有何积极意义?
该条款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对公司及全体股东:直接的财产追回与损失弥补。 当公司因财务造假遭受监管处罚、民事赔偿等巨大损失时,高管却拿着基于虚假报表发放的高额薪酬“全身而退”,这严重损害了公司和广大股东的财产权益。本条款赋予了公司直接的“追索权”,可以将这部分不当得利追回,直接弥补公司财产损失,最终惠及全体股东。
对董事、高管:强有力的行为矫正与精准惩戒。 该条款打破了“薪酬照拿、责任不担”的困局,将高管的薪酬与其真实业绩和勤勉尽责情况深度绑定。它形成了强大的法律威慑,促使董事、高管在履职时更加审慎,特别是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保持高度警惕,从源头上抑制其参与、纵容财务造假的动机,实现了“过罚相当”的精准惩戒。
对资本市场:强化公司治理与提振投资信心。 此规定是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司法举措。它向市场传递了明确信号:司法系统将严厉打击“劣迹高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这有助于提振中小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引导资本流向治理规范、诚信经营的公司,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二、该条款仅规定了公司有权提出请求,是否意味着投资者的请求权没有保障?在董事、高管控制公司的情况下,公司起诉存在障碍。
投资者的间接保障机制:股东代表诉讼。
该条款明确规定公司是请求权主体,这符合《公司法》的基本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的权利没有保障。当公司因受涉事董事、高管控制而怠于起诉时,《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就提供了救济途径。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通常是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涉事董事、高管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包括退回违法薪酬)。因此,投资者的请求权可以通过股东代表诉讼间接实现。
三、如何理解“退回与其业绩不相匹配的超出合理标准而获得的薪酬或者股权、期权”?退回薪酬年份与上市公司存在虚假记载或者隐瞒重要事实年份相对应?
退回薪酬的年份对应关系:原则上应对应。 最直接和合理的理解是,退回的薪酬应与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特定会计年度直接挂钩。例如,2023年度的财务报告造假,那么基于2023年虚假业绩而发放的年度绩效薪酬、奖金以及行权的股权激励等,应被列为追索对象。
但需考虑跨期影响。 有些薪酬方案(如三年期奖金、分期行权的期权)可能跨越多个年度,但其考核基准包含了造假年度的数据。此时,应进行合理评估,追索其中因造假数据而“虚增”的部分。
四、如何界定“与其业绩不相匹配的超出合理标准”?
这是一个需要综合裁量的问题,可以采用“两步法”进行界定:
第一步:确定“合理标准”。 可参考以下因素:①公司内部有效的薪酬管理制度及绩效考核办法;②同行业、同规模、同地区上市公司的薪酬水平;③公司历史上的正常薪酬水平;④公司薪酬委员会的意见。
第二步:识别“不匹配”的超出部分。 核心是进行 “业绩还原” 。即,在剔除财务报告中的虚假记载或隐瞒事项后,重新计算高管在该年度的真实业绩。然后,根据真实的业绩水平,对照薪酬制度,计算出其应得的薪酬数额。“实际领取的薪酬”与“基于真实业绩应得的薪酬”之间的差额,即为“与其业绩不相匹配的超出合理标准”的部分。
举证责任: 为减轻公司的举证负担,可以考虑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涉事董事、高管来证明其获得的薪酬与真实业绩是匹配的,若其无法证明,则推定公司请求退回的金额是合理的。
五、该条“违法薪酬退回”条款在实操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该条款目前的规定较为原则化,为确保其对司法实务的指引性,需要注意以下:
(一)请求权主体依赖股东主动起诉,投资者保护机构可参与进来
借鉴《证券法》关于投资者保护机构的规定,明确“投资者保护机构”,为维护公司利益,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或支持公司诉讼。这能极大增强条款的威慑力和可执行性。
(二)认定标准模糊,可能引发裁判尺度不统一
法院在认定“不匹配”和“合理标准”时应考虑的因素清单目前没有明确(如上文所述),所以,有必要鼓励使用行业专家、审计评估等专业意见辅助判断。
(三)行政处罚、刑事追责的衔接需要明确
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可将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已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为认定财务会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以及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的基础证据,除非当事人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
(四)关于追索的时效起算点
公司请求权行使的时效期间,可以是自“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财务会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隐瞒重要事实以及相关薪酬之不匹配性时”起计算。
总结而言, 第八十五条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立法进步,但其效力的真正发挥,有待于通过细化和补充,使其更具操作性,并通过激活股东代表诉讼、引入专业机构支持等方式,确保其可操作性及对现实的指引价值。
本文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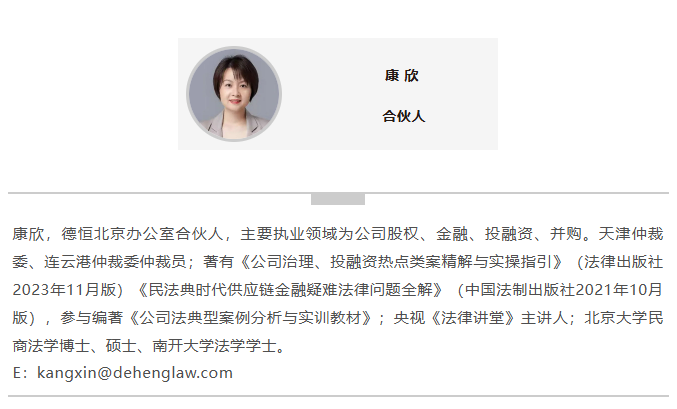
声明:
本文由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创,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德恒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