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法下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
2025-10-11
一、引言
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其董事原则上不对公司债务承担个人责任,这一原则构成了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石。然而,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复杂化以及董事职权的扩张,董事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可能因恶意或重大过失,直接或间接导致第三人遭受损害。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公司内部治理与外部第三人利益保护,成为公司法领域的重要课题。现行《日本公司法》第429条第一款,即“董事等执行职务时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的,则须对由此受损害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1]明确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律路径。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日本法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法律性质、责任主体与对象的认定、责任构成要件及其适用机制,并结合判例与学说,对该制度进行深入探讨。
二、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性质的争议
从法理上看,日本学术界对于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性质讨论大致可以分为特别法定责任说、修改法定责任说、侵权行为特则说以及和特殊侵权行为责任说,具体介绍如下:
第一,特别法定责任说[2]。该学说认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区别于债务不履行责任以及侵权行为责任,是一种特别的法定责任。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仅需证明损害与董事“任务懈怠”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董事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而无须证明董事是否存在对第三人加害的故意或过失。同时,该责任可与一般侵权责任竞合,其损害范围不仅涵盖直接损害,也应包括间接损害。
第二,修改法定责任说[3]。该学说认为,日本《公司法》第四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的适用范围限定于公司债权人的间接损害。直接损害可以直接通过侵权责任来进行救济。进一步解释来说,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规定类似于民法中的债权人代位制度,债权人可以基于该规定行使其对于董事的间接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股东的间接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可以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来进行救济。债权人和股东的直接损害赔偿请求权,通过民法中的侵权责任规定而不是通过本条规定来进行救济。
第三,侵权行为特则说。该学说主要由松田二郎法官主张,其认为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是侵权责任。在此基础上,董事对第三人的侵权责任与《日本民法》规定的侵权责任相比较,董事在职务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侵害责任,只有在董事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下才发生,一般过失的情形下并不发生,并且将董事责任的损害范围界定为直接损害,不包括间接损害。
第四,特殊侵权行为责任说[4]。该学说主张,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性质并非民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而是旨在强化董事义务的特别规定。该学说内部存在三种不同见解:第一种见解认为,损害范围既包括直接损害,也包括间接损害,并将“恶意或重大过失”作为判断是否构成任务懈怠的要件,同时承认其与民法一般侵权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竞合关系。第二种见解在损害范围及过错要件上与第一种基本一致,但特别强调股东损失应通过股东代表诉讼机制予以救济,且明确排除短期时效的适用。第三种见解则原则上将损害范围限定于间接损害。
针对以上学说的争论,昭和44年11月26日,日本最高裁判所大法庭[5]作出了以下判决:“董事因为恶意或有重大过失违反善管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给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只要董事的职务懈怠行为与第三人所受到的损害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不论是公司自身受到损害的结果使得第三人也受到损害的情形,还是第三人直接受到损害的情形,该董事都必须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上所述并不妨碍第三人通过一般侵权行为的规定,追究董事在履行职责情形中因为故意或者过失直接给其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但是,受到损害的第三人通过2006年修改前《日本商法》第266条之3的规定来追究董事的损害赔偿责任时,第三人只需要证明董事对职务懈怠行为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而无须举证其对自己有加害的故意或过失。”由此,日本判例支持了特别法定责任说,故该说也成为当今日本关于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性质的通说。
三、责任主体与对象的认定
(一)责任主体——董事的认定
《日本公司法》第429条第二款规定:“下列人员实施该各项规定行为的,也与前款相同。但其证明实施该行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的除外:
(1)董事及执行董事:(a)在募股等过程中就重要事项作虚假告知,或为募资目的就公司业务状况作虚假陈述或记录;(b)在财务报表、经营报告、附属明细表或临时财务文件中就重要事项作虚假记载;(c)虚假登记;(d)虚假公告(包括第440条第3款规定的措施)。
(2)会计顾问:在财务报表、附属明细表、临时财务报表或会计顾问报告中作虚假记载。
(3)监事、审计委员等:在审计报告中对重要事项作虚假陈述或记录。
(4)独立审计人:在财务审计报告中对重要事项作虚假记载。”
由此可见,《日本公司法》第429条的责任主体不仅涵盖董事,还包括会计顾问、监事、审计委员及独立审计人等。鉴于董事范围的不确定性且其在司法实践中成为追责的主要对象,本部分将重点围绕“董事”展开论述。
1.名义董事
名义董事,是指虽经合法程序选任、具备法律上的董事身份,但其与公司之间存在明示或默示约定,将全部职权交由他人行使,自身不参与公司经营的董事。由于名义董事是通过正式选任而产生的,其法律地位与其他董事无异。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名义董事实质上是将其名誉或社会影响力“出借”给公司使用,其是否应承担《日本公司法》第429条第1款规定的责任?日本司法实践通过董事对公司的业务监督义务,建立起名义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例如,日本最高裁判所于1980年3月18日作出的判决中明确指出,即使名义上担任董事且实际上未参与经营管理,但只要拥有董事的头衔,就有义务监督其他董事的业务执行,并且不应忽视任何不正当行为。如果名义董事违反监督义务,则可能会承担对第三人的责任[6]。
2.表见董事
表见董事,是指已因选任决议不存在或辞职等丧失了董事的法律地位,但尚未办理变更登记,仍在外观上具备董事身份的主体。原则上,表见董事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董事,因此不构成对公司的职务懈怠,亦不承担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7]然而,日本判例确立了以下规则:虽非公司董事但同意登记其就任意旨的,不得以登记不实对抗善意第三人,因而不能免除其作为“董事”应承担的责任。[8]
3.事实董事
日本司法实践进一步将“董事”的认定扩展至“事实董事”。例如,在名古屋地方裁判所2010年5月14日作出的一份判决[9]中,被告虽无董事头衔,却实际掌控公司经营决策,包括代表董事在内的管理人员均服从其指挥。判决指出,该被告虽非正式登记董事,但作为实际经营者管理公司财产,且公司全体员工均视其为实际经营者,应当被认定为“事实上的代表董事”,并应类推适用《日本公司法》第429条第1款规定。
(二)责任对象——第三人的认定
“第三人”通常作广义理解,泛指公司以外、因董事等执行职务行为而受损害的一切主体,包括员工、公司债权人、被侵权人等。这一宽泛解释有助于全面保护与公司具有交易或利害关系的各类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就间接损害赔偿而言[10],股东是否属于“第三人”的范围,日本司法实践存在区分处理。
原则上,股东作为公司成员,其利益损失通常被视为公司遭受损害,应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解决。例如,在雪印食品损害赔偿金请求案[11]之中,董事的过失行为导致上市公司业绩恶化和股价下跌,从而使所有股东受到损害。对此,判决指出,这类间接损害原则上应向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解决,从而弥补股东的损失。
特殊情形下,股东可以直接向董事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例如,董事通过虚假信息诱使特定股东增资或放弃权利,该股东可基于个人权益受损直接向董事主张赔偿。又如,福冈地方裁判所于1987年10月28日作出的判决[12]中指出,在闭锁型公司(閉鎖型公司)中,若存在股东代表诉讼无法发挥实效的特殊情况,则可能认可股东直接请求董事赔偿。具体而言,该案件中,被告Y是X公司的代表董事,也是大股东,所有董事成员都是Y的亲属。判决指出,在代表诉讼中少数股东的损失难以得到实际赔偿,故支持了股东对董事的损害赔偿请求。
四、日本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构成要件
根据现行《日本公司法》第429条第1款规定以及相关判例,董事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1)职务懈怠行为;(2)第三人受到损害;(3)董事主观上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4)职务懈怠行为与第三人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以下就前述要件展开分析。
(一)职务懈怠的行为
1950年《日本商法》修订前,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以“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为客观要件。1950年修法后,该客观要件被删除,董事责任范围随之扩大至违反一般性义务的行为,即包括勤勉义务与忠实义务。[13]就勤勉义务而言,现行《日本公司法》虽未直接规定,但通过第330条[14]准用《日本民法》第644条[15]关于委任关系的规定,要求董事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处理事务,此即“善管注意义务”。就忠实义务而言,《日本公司法》第355条明确规定:“董事须遵守法令、章程及股东大会决议,为股份公司利益忠实地执行其职务。”因此,违反上述任一义务,或存在其他违反法令、章程的行为,均可构成“职务懈怠”。
例如,在大阪高等裁判所2014年12月19日判决[16]中,一家公司明知无力偿债,仍签发支票采购商品,最终倒闭并致支票退票。判决指出,在公司财务状况极度恶化、处于债务超额或接近超额状态时,董事负有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债权人损失扩大的善管注意义务,包括评估重建可能性或适时进入清算程序。如董事仍进行无偿还前景的借款或签发支票,则可能构成职务懈怠,并应对债权人因此所受损害承担责任。
日本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构成职务懈怠,通常适用经营判断原则。经营判断原则尊重董事在合理范围内的商业决策自主权,只要决策基于合理的信息收集与决策程序,即便结果对第三人不利,亦不当然认定为职务懈怠。例如,在爱泊满损害赔偿案[17]中,公司董事会在收购子公司时,以高于评估价数倍的价格完成交易。一审、二审判决认为该收购价格缺乏合理依据,认定董事违反善管注意义务。但最高裁判所认为,收购价格的确定需综合考虑业务收益预期、收购顺利性、与原股东关系维持等多种经营因素,尤其对于非上市公司,董事在价格确定上享有较大裁量空间。该案中董事会已履行讨论程序并征求律师意见,决策过程无明显不合理之处,故不构成违反注意义务。可见,对于该原则的适用,日本裁判所通常对经营判断的过程与内容进行审查,重点包括董事在事实认定上有无疏忽、推理过程是否存在明显不合理、董事的判断是否严重偏离通常职业经理人应具备的知识与经验等。
(二)第三人受到损害
在日本公司法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所涉的损害,可分为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两种类型。直接损害,是指董事履行职务时因恶意或重大过失,未损害公司利益,却直接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产生直接损害的典型情形包括:公司债务/合同不履行、非法侵占建筑物、侵害著作权、违反股东大会决议拒不支付退休董事的退休金,以及以虚假信息诱使他人投资等。[18]间接损害,则是指董事的职务懈怠行为首先给公司造成损失,进而使第三人受损的情形,例如,董事放慢经营、从事自我交易等不当行为导致公司破产,从而使债权人利益受损。[19]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公司债务或合同不履行,一种常见情形为公司已濒临破产,董事明知根本无法偿还借贷金钱或在无法支付价款的情况下,购入商品给交易第三方造成损失。[20]例如,在一起债券交易纠纷案[21]中,A证券公司资金状况严重恶化,在自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仍进行一系列违反行业自律规则的债券交易。东京地方裁判所认为,该公司的代表董事Y1等人,明知公司资金周转极度困难且相关交易违规,却未履行其监督公司合规经营的义务,放任违规交易发生,最终导致交易相对方的损失。最终,裁判所认定,Y1等人至少存在重大过失,未尽到监督防范违法交易的义务,构成职务懈怠,故应依当时《商法》第266条第3款第1项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又如,以明显且可预见将导致破产的方式持续经营公司,同时仍不断产生新债务或向无法获得商品或服务的客户收取预付款。具体表现为:Y公司的代表董事Y1实施了一项不当商业策略——尽管已意识到住房需求下降和材料成本上升,仍承接亏损订单,依靠客户预付款来获取现金流。该策略可预见地导致公司无法履行大量订单,并最终破产。因此,客户X1支付的预付款无法返还,贸易债权人X2的应收账款亦无法收回。本案中,代表董事的行为对客户X₁构成直接损害,即Y1在明知或应知Y公司已无履约能力的情况下,仍继续收取X1等人的预付款,该行为具有恶意或至少构成重大过失。X1所损失的预付款,是Y1不当行为直接导致的损害后果。代表董事的行为对贸易债权人X2构成间接损害,即Y1的整体经营失策直接造成公司资不抵债,进而使X2等贸易债权人的债务无法清偿。若该经营行为被认定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Y1须对X2因公司破产所遭受的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2]。
此外,日本平成年间的诸多判例表明,对于已处于事实破产状态的公司,若董事仍签订明显无法履行的合同,导致新的债务产生,法官通常综合考量公司的发展历程、历年损益、行业状况及已采取的改善措施等因素,以判断董事是否应承担责任,仅以公司破产时间与合同签订时间相近为由认定责任的情形较为少见。[23]在部分案例中,法官亦曾基于公司已实施具有实效性的经营改善对策,而否定了董事的责任。[24]
(三)董事主观上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
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须以其主观上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为要件。所谓“恶意”,系指明知行为不当或有意造成损害。例如,在舞蹈教室损害赔偿案[25]之中,大阪地方裁判所认为:Y公司在其经营的社交舞教室中播放CD等音像制品,侵犯了管理这些音像制品中所收录音乐作品著作权的音乐著作权管理公司X的作品演奏权。Y公司的代表董事自身也是舞蹈教师,负责指导顾客,鉴于代表董事的地位和职责,可以推定其明知或极容易知晓Y公司未经X公司许可使用管理作品,故代表董事的恶意失职行为给第三方X公司造成了损害,其应承担赔偿责任。
“重大过失”则指严重违反注意义务,其程度远超一般疏忽,通常表现为未尽到一名谨慎董事本应履行的最基本职责。例如,在高尔夫球场重建案[26]之中,Y公司代表董事Y2与董事Y3在未充分调查市场状况、亦未制定合理资金计划的情况下,即推动重建经营困难的高尔夫球场,企图依靠新会员入会费筹措资金。最终项目失败,新会员预付金无法返还。判决指出,董事在开展涉及众多利益相关方的大型项目时,负有事先充分调研、制定客观可行资金计划的基本义务。Y2与Y3未履行该义务,盲目推进项目,虽不构成恶意,但其行为已属重大过失,应根据《日本公司法》第429条对原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四)职务懈怠行为与第三人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昭和44年的最高裁大法庭判例[27]明确,无论是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害,只要“董事的职务懈怠行为与第三人损害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董事就应该直接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日本学界围绕“相当因果关系”的具体内涵与适用进行了诸多深入讨论。囿于篇幅,在此不予展开。
对于直接损害,因果关系的认定相对直观,如董事侵犯著作权,其行为与著作权人损失之间即成立相当因果关系[28]。对于间接损害,即首先损害公司利益进而影响第三人,因果关系的认定更为复杂,通常要求董事的行为显著提升了损害发生的客观可能性,且该因果关系未因其他异常因素的介入而中断。例如,在金融机构代表董事违法放贷致使公司资不抵债,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案例中,若该违法行为直接导致公司偿付能力丧失,即可认定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反之,若公司损失主要源于不可预见的系统性风险或市场剧烈波动,则可能切断因果链条。
五、责任机制的争议与适用
关于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形式,日本公司法在实践中主要涉及两种责任关系:一是董事与公司之间的责任形态,二是多名董事之间的责任分配。
在董事与公司的对外责任关系上,日本公司法更倾向于将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界定为一种单独责任[29],而非法定连带责任。这一制度取向可从立法沿革与司法实践中得到印证。在立法层面,1950年《日本商法典》第266条之三曾明确规定,董事“对第三人也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随着公司法数次修订,现行《日本公司法》第429条则规定“该董事对第三人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删除了“连带”的表述。这一措辞转变,体现出立法者对董事责任独立性的确认,强调董事应就其个人具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的职务懈怠行为直接向第三人负责。在司法实践中,第三人直接起诉董事请求赔偿已成为常见的追责路径。在认定责任成立时,裁判所通常直接判令董事个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不再以公司共同担责为前提。即使在少数案件中判决公司与董事共同承担责任,其法律依据亦非源于《公司法》第429条,而是基于《日本民法》中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定[30]。
在董事之间的内部责任关系上,现行《日本公司法》第430条的规定:“管理人员等对法人或第三方造成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且其他管理人员等也承担该损害赔偿责任的,此等人成为连带债务人。”[31]可见,当同一损害后果由多名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共同导致时,这些责任人应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此项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地保护第三人利益,债权人有权向任何一名负有责任的董事请求全部损害赔偿,而无须受制于董事内部责任分担的问题,从而显著提升了债权人获偿的实效性与便利性。
六、结语
总体而言,日本法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通过《公司法》第429条为核心,结合丰富的判例实践,构建了一套兼顾公司自治与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平衡机制。该制度以“特别法定责任”为法理基础,将责任主体扩展至名义董事、表见董事及事实董事,并通过“恶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与“相当因果关系”的限定,既为董事提供了合理的经营判断空间,又为受损害的第三人提供了有效救济途径。这一相对成熟的责任体系,对于完善我国公司治理及相关立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日本公司法》第429条,可见于:https://lawzilla.jp/law/417AC0000000086?n=ln979。
[2][日]铃木竹雄:《新版公司法》,弘文堂全订1980年版,第151页。
[3][日]吉川义春:《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日本评论社,1986年。[日]吉川义春: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理论问题》, 《立命馆法学》第五·六号。
[4]陈景善:《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认定与适用中的问题点——以日本法规定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5期,第95页。
[5]最判1969年〔昭和44年〕11月26日判决〔民集23卷11号2150页判例〕。
[6]最判1980年〔昭和55年〕3月18日判决〔判例时报971号101页〕
[7][日]山本为三郎著,朱大明等译,《日本公司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8]最判1972年〔昭和47年〕6月15日判决〔民集26卷5号984页〕;最高裁判所〔昭和62年〕4月16日判决〔金融・商事判例778号3页〕
[9]名古屋地判平成22年5月14日,判时第2112期第66页。参见吴建斌编译:《日本公司法 附经典判例》,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36页。
[10]注:日本通说认为,在直接损害赔偿中,股东属于“第三人”之范围。
[11]东京高裁2005年〔平成17年〕1月18日判决。
[12]日本公司法中董事對第三者的責任:公司法第429條與主要判例解說,可见于:https://monolith.law/zh-tw/general-corporate/director-thirdparty-liability-japan。
[13]陈景善:《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认定与适用中的问题点——以日本法规定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5期,第94页。
[14]《日本公司法》第355条:股份公司与公司负责人以及会计监查人的关系,服从有关委任的规定。可见于:https://lawzilla.jp/law/417AC0000000086?n=ln979。
[15]《日本民法》第644条:受任人的注意义务:受任人负依委任的本旨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处理委任事务的义务。可见于:https://hourei.net/law/129AC0000000089。
[16]日本公司法中董事对第三者的责任:公司法第429条与主要判例解说,可见于:https://monolith.law/zh-tw/general-corporate/director-thirdparty-liability-japan。
[17]最判2010年〔平成22年〕7月15日判决〔民集第234号225页〕。
[18]陈景善:《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认定与适用中的问题点——以日本法规定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5期,第98页。
[19]陈景善:《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认定与适用中的问题点——以日本法规定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5期,第97页。
[20]周剑龙:《废除公司最低资本金制度情形下的公司债权人之保护——以日本法上的公司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为视角》,载《商事法论集》2015年第2期,第254页。
[21]东京地判2003年〔平成15年〕3月19日判决,判时1844号117页。
[22]Japanese Attorney at Law - Bengoshi L.L.,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Can Directors of a Japanese Company Be Held Liable to Third Parties?” 2025年5月31日,https://japancompliance.com/under-what-circumstances-can-directors-of-a-japanese-company-be-held-liable-to-third-parties/。
[23]中村康江:《取締役の第三者に対する責任——任務懈怠—会社の契約不履行》,総合判例研究10,第358-382页。
[24]东京高判1989年〔平成元年〕1月28日判决〔判例集第723号第243页〕。
[25]大阪地判2002年〔平成14年〕9月5日判决,LEX-DB文献编号28072737。
[26]东京地判1995年〔平成7年〕4月25日判决。
[27]最判1969年〔昭和44年〕11月26日判决〔民集23卷11号2150页判例〕。
[28]东京地判2002年〔平成14年〕6月28日判决,〔判例时报第1795号第151页〕。
[29]叶名怡:《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性质》,载《法商研究》2025年第4期,第134-152页。
[30]大阪地判2003年〔平成15年〕10月23日金判1186号44页。
[31]《日本公司法》第430条,可见于:https://lawzilla.jp/law/417AC0000000086?n=ln979。
本文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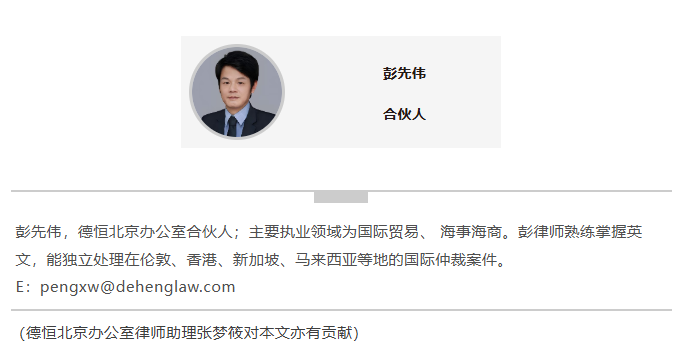
声明:
本文由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创,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德恒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
